徵信社-戳穿了他妻子的外遇
徵信社-戳穿了他妻子的外遇
麥芽身材瘦長,一身顏色淡雅的純棉的休閒裝,一雙土布面的平底鞋,未施脂粉的臉上,清瘦、放鬆,還有一點倦怠,不像一個35歲的女人的除了她的神態,還有她那雙顧盼生輝的眼睛。我們因為約稿的事情相識,後來事情沒成,卻發現聊起來非常投緣,她說自己現在還是獨身,聽說我在採訪獨身女性,她馬上笑說最近好像突然有個新詞叫“北大荒”——北京(北)的大齡(大)未婚,(荒)女人,那她算是“北大荒”群中名副其實的大姐大了。
十年前和十年後,我都沒覺得獨身是什麼嚴重的個人的不幸。我一直都覺得婚姻是愛情的必然結果,而且還要是一場猛烈的徵信愛情。雖然不斷有人告訴我,你一定要想明白了,你到底要的是愛情還是婚姻?如果你到這個年紀了還一心追求愛情,那你別想有婚姻。我確實是個愛情至上主義者。這一點在我25歲時如此,在今天仍然如此。
25歲的時候,我讀完碩士,從一所全國重點大學畢業了,專業是中文。畢業後服從分配到了一家不錯的報社,做編輯兼記者。
一年以後,報社派我到山西臨汾採訪一個新長征突擊手。他是一位年輕的礦長,上任五年,把一個小煤窯打造成一個優秀企業。他們礦上派了一個小伙子負責接待,安排我的採訪日程,陪著我到處跑。
剛認識不久,他就問我,麥記者,你的孩子多大了?我說,我沒孩子。他又問,那你的愛人也是記者嗎?我說,我沒愛人,我還沒結婚呢!他立刻滿臉通紅直道對不起,我說沒什麼,你呢?他說,他21歲了,去年結的婚,現在老婆已經懷孕了,他們兩人都想要個兒子。還發愁地說,由於不認識人,照了B超人家也不告訴懷的是男還是女。我說,生男生女還不都一樣嘛,反正都是自己的孩子。他說,生男生女不一樣,就是不一樣,你還沒結婚當然不知道了。然後,他問我,麥記者,你多大了?我說我比你大5歲。他吃驚地說,哎呀,真看不出來,麥大姐,你可得趕快成個家啦!此後,他陪我去採訪,介紹我的時候,總是在介紹完我供職的單位之後,再加上一句:“麥大姐現在還獨著身呢”,同時還回頭重新打量我一下。如今,十年過去了,我還清楚地記得他說這句話時的神情。那是滿臉的疑惑、感嘆和不理解,一字一頓地完全像在介紹一個天外來客。
但是,現在,10年過去了,我依然獨身著。這10年對於一個女人意味著什麼?一段生命中最好的年華,最璀璨的青春歲月。
十年前和十年後,我都沒覺得獨身是什麼嚴重的個人的不幸。我一直都覺得徵信婚姻是愛情的必然結果,而且還要是一場猛烈的愛情。雖然不斷有人告訴我,你一定要想明白了,你到底要的是愛情還是婚姻?如果你到這個年紀了還一心追求愛情,那你別想有婚姻。
我確實是個愛情至上主義者。我的原則是跟著感覺走。可跟著感覺走又怎麼樣了呢?
大學時代據說是談戀愛的黃金時代,大學校園裡到處都是成雙成對的男男女女,但我那時是絕對看不上那些嘴上黃毛還沒褪淨的小男孩的。於是25歲畢業的時候,居然還沒有男朋友。幸虧父母一直在中央美術學院當老師,看慣了年輕人的荒唐事,思想也開明得很,對我的個人生活問題從未施加過什麼壓力,我也一直在家裡做父母的膝下嬌女。這種寬鬆的家庭環境也為我後來多年的獨身生活建立了一個堅強的後盾。
大學畢業以後,我就進入一個廣告公司做文案徵信社,成熟而有魅力的中年男人自然也很方便地遇到了。當然,他們都是已婚人士。也許因為年輕,也許因為我的性格,和我交往的幾乎都是已婚男人。雖然有過幾段驚心動魄的感情經歷,最終也因為無法長相廝守而曲終人散。去年,也是在初秋時節,我在拾荒者認識了吞吐。
當然,吞吐是我給他起的外號,或者說叫愛稱。他特別能喝啤酒,就像一駕吞吐量特別大的啤酒機。拾荒者你知道吧?據說拾荒者這個酒吧是專為單身族設計的,從桌子板凳到小擺設,再到飲料酒水和小吃的名稱,處處都是為心境荒涼、情感飢渴的曠男怨女們定做的。我最初慕名而去也是出於一份好奇,但很快就發現,去拾荒者的各色人等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心無所屬——這遠遠不是單身一族的專利,而且,像我這樣喜歡獨來獨往的人,不可能與任何人交談,也就不會知道他們到底是不是獨身,也不必知道。
我總是在午夜時分去拾荒者喝一杯。白天,你根本不會注意到什麼拾荒者。它的門面不大,那種懷舊式的設計風格顯得頗為落寞和殘破,似乎門可羅雀。可當夜幕降臨的時候,它就突然成為一曲循環往復的小夜曲,你總覺得你一腳進門就能曲徑通幽。
吞吐又說:“噢,請來一杯,要三分之一泡沫,謝謝。”
我想這準是個挑剔的傢伙。但吸引我的還是他的眼睛。他那目光與那裡的氣氛真是太格格不入了。
只要你去一次就能感覺到,子夜過後,拾荒者是暗香浮動,倩影多姿,到處是渙散的激情,到處是紙醉金迷之後的慵倦徵信社,是一個無始無終的場所。而這個人的目光太清澈,太專注,像一針清醒劑。可是在拾荒者,我即便不想買醉,也絕不想清醒!
很快,魯魯就把一杯啤酒放到他的跟前:果然是他要求的三分之一泡沫。像這樣對啤酒如此挑剔的人並不多見,魯魯顯然是來了精神。這個人舉杯的模樣有點煞有介事。他將杯沿貼近唇邊後並不馬上喝,而是深深地看一眼魯魯,然後慢慢喝下一口。
那一天午夜,我照例在結束一個很困難的採訪以後去了拾荒者,也照例直奔吧台,目的單一,周圍嘈嘈切切的低語聲和歌手們的輕歌曼舞概不入耳。當我在吧台前註意到吞吐的時候,我其實已經準備打道回府了。
只聽他在問魯魯有沒有德國迷你啤酒。魯魯堪稱拾荒者的頂樑柱。他是京城數一數二的調酒師台北市徵信,有不少酒吧都想高薪把他挖走,但他死心塌地地呆在拾荒者,因為那裡有喀秋莎。喀秋莎是從俄羅斯來的打工妹,說著一口流利的漢語,那副金發碧眼的模樣足以用上什麼“閉月羞花”、“沉魚落雁”之類的經典詞句。吞吐當時詢問的聲音有些拿腔作調:“先生,請問有德國迷你啤酒嗎?”
我不由得抬眼看他。他的面孔白皙,眼睛有一點點凹陷,身材高大,身體繃著一股勁兒,從穿著到神情都顯得與拾荒者格格不入。
正在吧台前忙活著的魯魯歡快地打著呼哨,說“喔塞!你真是找對地兒啦”!
呵,還真不錯。他點頭稱讚了一句,但魯魯並不罷休,還是疑問地盯著他。於是,他又喝了一口,說口味相當純正。然後,他就微笑起來,仰脖子把一尊啤酒都喝乾了。
在這個過程中,我發現他和魯魯的眼神裡都有一種孩子氣的挑戰和期待。我忍不住“噗嗤”一聲笑了。我想魯魯未免頭腦簡單。既然要鄭重其事,那麼,他怎麼就能斷定眼前這個生客就真有如此這般的發言權呢!他們兩人簡直就是在玩拉鉤上吊的遊戲嘛。沒想到,我這一笑他就接了話茬,他正色地說,“小姐,你別笑台北市徵信社,我在北京找到這樣純正的德國啤酒還真不容易。”他一臉認真,聽上去對我的笑不以為然。
這樣一來,我對他產生了興趣。你知道的,我也是一種“偏要喝這一口的人”。我成為拾荒者的常客,就是因為魯魯調製的馬爹利正合我的口味。我說,噢,看來咱們都很在乎酒的口味。你喜歡德國的迷你啤酒,而我獨愛這裡的馬爹利。他說,那你跟我老婆有一拼。我老婆也特喜歡馬爹利甚麼的,結果就回國來專門推銷洋酒了。我說,那你就是推銷迷你的啦?他說不是。他在德國工作好幾年了,現在是邊工作邊讀碩士學位。為了做論文,所以回國來做調查。
吞吐是學釀造專業的。這次回國是專為一家德國公司做可行性報告,看看在北京可不可以建設一個啤酒城。我不認為在北京建設一個啤酒城有特好的前景,因為我已經做了好幾年的經濟記者了,對投資這種事有起碼的判斷力。但他很自信,說他們規劃的啤酒城不是國內的人能想像的。他們要搞豪華的,打文化牌,從德國進口整套的大型流水線,營造一個不僅有純正的德國啤酒,還有舒適的各種享受,高雅的文化沙龍,甚至可以演歌劇,從設施、管理、服務,到具體的內容,什麼都是歐化的。就這麼你一句我一句地閒聊著,我們就熟悉起來了。我注意到已經有幾大杯啤酒下了他的肚,他不僅臉不變色心不跳,而且也沒去過一次衛生間,那些啤酒全都沒了踪影。而我,又喝了兩小杯馬爹利,已經有點醉了。我就說我該回家了。他把杯中酒喝乾,說那我送你吧。我說,如果你沒開車,那我就送你吧。他吃驚地說,你開什麼玩笑,你喝了這麼多酒。我說,我的毛病是一握方向盤就清醒了。
我把他送到了家門口的時候,已經是第二天的凌晨了,他卻並不急著下車,而是毫不遮掩地凝視著我,邀請我上樓去喝杯咖啡休息一下。我知道上去以後會發生什麼,我並不害怕,只是確實累了。所以,我婉謝了他的邀請。
可是,有時候緣分來了你躲也躲不過的。我們就開始在那一天太陽升起之後,也就是我們在他家門前分手以後的幾個小時。
那天早晨我一覺醒來,覺得有一點頭疼,也許是有點宿醉台中市徵信,懶洋洋地不想起床。想一想當天沒有必須去參加的會議,也沒有約什麼採訪,手邊一個沒開始的稿子也不必立刻交稿,索性就鬆弛下來。雖然其實只睡了幾個小時,但睡得卻很沉,夢中的人和事還在絲絲縷縷地藕斷絲連,彷彿如有所使,一陣陣淡淡的空虛掠上我的身體。我穿著睡衣,晃蕩下樓,取回吞吐的名片,給他的手機發了一條短信,跟他說我現在精神抖擻,你在幹什麼呢?他的回复既迅速又簡潔,就是“我已恭候多時!”
我憑著記憶驅車去他家,他已經站在了那個樓門口。我突然好像已經忘了他長什麼樣子了,隔夜在拾荒者的相識恍如一夢。但幾乎就在一錯目之間,我從他的眼睛認出了他。不錯,就是這種目光。在白嘩嘩的陽光下,他又是毫不遮掩地凝視著我。他的眼睛清澈深邃篤定,在沉靜之中蕩漾著不易覺察的激情。彷彿時光倒轉,凌晨時分我們並沒有分手。就是這幾秒鐘的對視,我知道有種東西我無法抗拒,那就是愛情。
這就是一見鍾情吧?
有了那種出生入死、由死而生的開始,我和吞吐不能停止相親相愛。
總是以為青春早就不屬於我了,長久以來,我不斷地跟自己說,我只盼望寧靜久遠的愛情,那是特為婚姻準備的。但我和吞吐,突然就毛手毛腳地漲滿了,開始了,而且持續著,就像一對處子轟轟烈烈地跌進情網。我總是反複審視狂歡之後落入黑甜鄉中的他,為的是擔心我是不是為他的眼睛所騙。
吞吐的皮膚過於白皙細膩,和他那男性化的高大身材頗不匹配。然而,他的眼睛確實是他的肉體和精神的代言。他靜如男孩兒的身軀在被點燃之時迅即爆發為奮不顧身的孤注一擲,比我曾經熟悉的黝黑的狂野更加令我驚詫和折服。在奔射的那一刻,他釋放在徹頭徹尾的忘我的陶醉中,我在力量的消耗、粉碎和極度的放任中痛感生命的存在。我變得很貪婪,完全像小女孩的時代貪吃外國巧克力。
直到冬季,一天夜裡在拾荒者,他才老老實實地談起我們的邂逅和相識。他說自己只是短期回國,並不想感情出軌,而且,坦率地說,他不喜歡愛酒的女人。但那天夜裡,偏偏是我開口對他說話。我的聲音斷斷續續,眼睛忽明忽暗,有那麼一種東西,他也說不清,總之,就有了以後。
自從與吞吐約會,每個週末我都過得不像一個單身女人。除了有時去看看父母,他總是會和我共度週末的,好像一個快樂的單身漢。我要是問你老婆呢?他總是說她很還忙,她推銷洋酒要見很多人的。我說,難道她忙到連周末都要跟客戶在一起嗎。他就嘲笑我說,什麼週末不周末的,自己當老闆的人,哪有什麼週末的概念呀!要是問得多了,他就會不耐煩,嗔怪我說,你老問她幹嘛,你不願意我陪著你呀?我也不示弱,反齒相譏地說,哼,你陪著我?只怕是想陪你老婆陪不上吧!他不樂意打嘴仗,每當帶點刺兒的話從我嘴裡一出來,他都會一把摟住我,用他的嘴堵住我的嘴了事。我也並不再深究。我知道,認真著又不認真才是我的認真。再說,平時見面都是行色匆匆,週末,我們才能放鬆地聊天、泡吧,或者開車出遊,我閒閒散散的,只把這一切當成一次次舒服的小憩。
就這樣,我和吞吐的約會持續了一年多。如果不是突然有機會見到了吞吐的老婆,日子會一如既往,在永遠的假像之中只知開始,不知所終。
那是一個由輕工業局舉行的大型品酒會,我作為記者出席。
說是品酒會,其實也是一個招商會,一個酒商和客戶的見面會。我只轉洋酒區。拿資料,看到誘人的酒就嘖一口,台中市徵信社在人頭攢動中尋找著新聞亮點。一種前所未聞的葡萄乾邑吸引了我,我饒有興味地準備品嚐一下。剛剛舉起杯,一個人突然站到了我的面前,大呼小叫著:嘿,果然找到你了!我一猜你就會在這個展區。我遇到吞吐了。他滿臉含笑,興沖沖地拉住我說,走,我帶你看看我老婆的展位。他拉著我三腳並作兩步地走,說他早就來了,都在啤酒區轉了好幾趟啦!還說,這裡展出的外國的啤酒太少啦,德國啤酒種類多了去了,這裡卻只有二三種!我對啤酒不感興趣。就問他老婆做得怎麼樣。他更興奮了,說她幹得很不錯,才乾了兩年,就有了不少訂單了!
我們很快就到了他老婆的展位。她那展位佈置得十分精心,有明顯的女性色彩,而且,我不得不承認,還不落俗套。她老婆呢,長像頗為艷麗。一身酒紅色的職業裝一看就是舶來品。這是我第一次見他老婆,也是最後一次。她有一頭烏黑的長發,燙成老派的大波浪式。她臉上的妝偏濃,皮膚光潔發亮,一望即知經過美容院小姐的打理。她的十指也經過專業修剪,塗成淡粉色,也在閃閃發光。這是一個刻意保養和修飾的女人。雖然顯得有點矯飾或誇張,但她站在造型各異、形狀別緻的洋酒和高腳杯中間,十分協調。後來我知道,她比我年長三歲,比吞吐小二歲。
吞吐落落大方地把我介紹給他的老婆。稱我是一個懂行的“名記”,說她是洋酒推銷業的未來之星,我們一起一見如故似地哈哈大笑。但她並不滿足於吞吐含糊其辭的介紹,而是仔細問了我供職的報社,要了我的名片,問了我對此次品酒會的看法,並說她是第一次參加這麼大型的品酒會,要我談談對她的展位的感覺,然後,才開始介紹她經營的酒。
聽畢她嫻熟的介紹,我沒有應她的要求品嚐那些晶瑩剔透的洋酒,卻去看被醒目地噴印在展台兩壁的照片。這是一些商務照片,被錯落有致地組接在一起,她在其中變換著各種服裝,和不同的人握手、簽約、合影,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是笑容可掬。就是在這個時候,一個熟悉的面影抓住了我不經意的目光。
那是一個年過半百的男人。微胖,西服革履。在這組照片中,他出現在兩張合影上,她也兩次站在他身邊。不,並沒有緊靠或依偎什麼的,恰恰相反,當其他人都挨在一起合影時,他和她之間留著一道謹慎的縫隙。但她就是在這兩次打破了常規的、職業化的笑容可掬:一次縮肩大笑,一次面無表情。
我並不是具有偵探細胞,也不是斷定不與丈夫一起度週末的女人一定紅杏出牆,而是我們都太知道這個男人。他來自台灣,經營著一家合資酒店。他的酒店原來是二星級,據說已經批了或正在批三星。他在上海還有一家酒店,由他老婆主管,他的孩子也在上海。他的緋聞不斷已經不是什麼秘密,也已經引不起人們的興趣了。
見我在照片前駐足,他老婆就上前來指著那個男人介紹說:“你知道吧?他的酒店經營得很出色,現在我和他北京和上海的酒店都有業務,可能很快就會跟他台灣的酒店簽約”。說著,她兀自展顏一笑,說:“這可是商業秘密呀,你可千萬別給我曝光呀”!
看著她那幅神采飛揚的表情,我內心突然一動,想起我的初戀情人愛說的一句話:你沒吃過豬肉還沒看見過豬跑嗎!一個想法,或者說一個計劃就在那一刻誕生了。
我要是告訴你我的這個想法或計劃,你可別說我陰呀,其實,我並不是有心計的那種女人。
我是一個資深記者,朋友很多。他老婆身邊的那個男人又是業內的一個公眾人物,我沒怎麼費勁就打聽到了他們的隱私。他們兩人確實不僅僅是客戶的關係。一個我認為是準確的消息很快就來了,明天,也就是周末,他們要一起去參加一個在瑞士大使館舉行的酒會。
酒會大約在晚上九點結束,他們將去約會,地點在香格里拉飯店的***房間。
週五早晨,我一到辦公室就給吞吐發信。我們的編輯部總是熱鬧非凡。幾百號人均勻分佈在一個開放的辦公空間裡,呼機、手機、電話聲此起彼伏,編輯們的高談闊論、送快遞的吆喝一聲高過一聲,整個一個人喊馬嘶,給吞吐發E-mail更方便些。我約他當晚九點半到香格里拉飯店的***房間見。他很吃驚地問幹嘛換地方。他說他需要等一個德國的電話,很重要,讓我先到老地方等他。我堅持要換到這個地方,而且時間也不能改,結果他同意了,我也鬆了一口氣。他自然渾然不覺,畢竟,再心有靈犀的情人,他也不是我肚裡的一條蟲。
那天晚上八點鐘的時候,我又確定了一下消息,還給吞吐打了一次手機,跟他約定不見不散。然後,我就坐在自己的小隔斷裡描眉化眼。通常上班什麼的工作場合,我都化淡妝,而且相當精心。一個35歲的單身女人,已經老到不能靠天生麗質素面朝天了,但又還沒老得要以撲粉掩蓋年齡。那個週末的晚上,我第一次發現我有了淡淡的黑眼圈。當然是因為經過一天焦頭爛額的工作,還有前一夜的失眠。前一天夜裡,我一直想著我的計劃,想著我真要捅破馬蜂窩了,搞得徹夜輾轉難眠。用通常的淡妝已經很難不洩露我滿臉的疲憊,於是我把妝加重了一些。往常和吞吐約會,我是不化妝的,他喜歡我本來的樣子,而且他是我最理想的靈丹妙藥。
九點鐘的時候,我到了拾荒者。太早了,拾荒者裡靜悄悄的。一個中年男人坐在遠處角落裡那個靠牆的位子,正在認真研究菜單;一對年輕的情侶一人面前一杯花花綠綠的冷飲,腦袋貼在一起。魯魯和喀秋莎坐在吧台後面,小聲聊著天。他們抬頭見到我,臉上掠過意外的表情。我簡單地朝他們打個招呼,仔細選擇了一張靠窗的桌子。喀秋莎近前來,問我是不是要一杯加冰的馬爹利。我改要了一扎迷你啤酒,還點了幾樣點心。
我特意關了手機,專心致志地頻頻看表。吞吐約會總是遲到的,因為他總是對北京塞車的嚴重性估計不足。而這一次我是注定不會赴約的。在那個豪華房間,出現在他面前的將是他的妻子,和另一個男人,那個三星級或二星級賓館的老闆。他們定期在那裡開房間,吞吐看見的只不過是一次“例行公事”。
我不斷地設想著可能發生的各種情況,也拿不准我和吞吐以後還會不會繼續下去。在一派胡思亂想中我吃完了點心,初次領教的迷你啤酒卻喝了幾口就喝不下去了。在昏暗的燈光中,我注意著每一個進來的人,不由得替吞吐擔心。我只希望他看到一個真實的場面,而不希望把事情搞得很激烈。我就這樣一直等了他三個小時!
子夜過後,拾荒者在漸漸升起的喧嘩聲中墮入了狂歡。我抬手叫喀秋莎,準備還是喝回我獨愛的馬爹利,正好一眼就看見吞吐徑直朝我走了過來。他走來的姿勢和進拾荒者的任何人都不同,就跟我在這裡初次見他的時候一樣,他好像永遠與這裡庸倦、松懶的氣味格格不入。
我對走到跟前的喀秋莎說來杯馬爹利,然後又轉向他問“給你來杯迷你嗎”?他說,不,也來杯馬爹利!他的聲音極端平靜。我小心翼翼地撩了他幾眼,叮囑喀秋莎把酒稍微搞濃一些。他並不搭話,坐下以後就只把兩眼緊緊盯向窗外,我看不出他的神情。
兩杯馬爹利很快就送來了。我嘖了一口,馬爹利給我的感覺還是如此美好。他也探索般地來了一口。見他並沒有張口的意思,我就只好打破沉默。我問,怎麼樣,馬爹利的濃度就是與啤酒的濃度不同吧?他不回答。我又問,你怎麼這時候才來?我還以為你不來了呢!他還是沒吱聲。我一著急,脫口而出地說:“哎呀,你是不是被人灌了啞藥啦”?他突然噗嗤笑了,然後聲音平靜地說了一句話。你猜他說什麼?他竟然說:“你今天怎麼抹這麼紅的口紅啊”?
你今天怎麼抹這麼紅的口紅啊?我剛才跟你說了,我這個晚上臨去拾荒者之前,在辦公室化了比較濃的妝。一瞬間,我完全相信,我得來的信息有誤,或那對男女突然改變了計劃,他並沒有看到我預謀他將看到的。不,不是我預謀,而是我引領。我當時有一種無可名狀的失落感!但是,緊接著又聽到他又抱怨,“你幹嗎整個晚上都不開手機呀,搞得我還得當面來向你道謝。”我聽出他的聲音裡有一點點譏諷,但我一時完全搞不懂他的真正用意。也許是看到我滿臉茫然,他點了一根煙,直截了當地問,那個男人是誰?這是我第一次看見他抽煙。他抽煙的樣子彷彿是在把滿腔的鬱悶一口一口地噴出來。見我沒有立刻回答,他又問了一次,那個男人是誰?我回不過神來似地也問了一句,你看見他們啦?
他瞥了我一眼,目光十分鋒利。我嘆了口氣說,你真的不知道嗎?那一天在你老婆的展台上有他的照片呀。他說,我怎麼沒注意?我說,是許多人的合影,那個男人在其中,你老婆在他身邊。他說,我老婆跟好多男人照過合影的,你怎麼就單單發現他和她有事呢?我說,並不是我一個人知道那個男人是怎麼回事,我只不過需要問一下他現在跟哪個女人在一起就行了!他說,那你告訴我不就成了,幹嗎這樣騙我自己去看呢?讓我傻呵呵地一頭撞進去,要真是去抓奸的倒也罷了。結果我興沖沖地出現在他們面前,一手舉著鮮花,一手拿著一瓶酒,還是你愛喝的馬爹利,好像是專程去給人家慶賀的!他說到這裡,我忍不住大笑了起來。我一邊笑一邊說,誰讓你整天說你老婆這兒好那兒好的!我就是想讓你明白,她不是你說的那樣!
他又瞥了我一眼,一口喝乾了還剩下的多半杯酒,向我伸出手來要車鑰匙。我一時沒反映過來,問幹嘛?他說,你說乾嘛,你害怕啦?他的眼睛彷彿乾枯塌陷的河床,燃燒著空洞的熱情,我看出慾望在不知不覺間變質,但如論如何,我不願退縮。儘管我知道,這裡不是一個開始的地方。經過白天漫長的等待,拾荒者孕育著一個響亮但無奈的結尾。在這裡,為了結束而盡情喧囂之後,誰都無力重新開始,我和他也不能例外。
吞吐開著我的車,飛快地到了他家。
那時已經是凌晨四點了,天很快就要亮了。在半明半暗的天色中,室內的一切都被籠罩在曖昧不明之中。
這是我第二次到他家。他說這所三室二廳的公寓房全是他老婆回國創業後辦的,是她付的首期,也是她在月供。她另外還在梅地亞租著一個相當於三室一廳的公寓式的房間,用來辦公,也可住宿。
我們兩個人都懶得說話。
他把車鑰匙啪地甩在鞋櫃上,一邊換他自己的鞋,一邊從鞋櫃裡給我找出一雙拖鞋。
第一次到他家時,我就認出這個鞋櫃和所有室內的家具、擺設都來自宜佳。他說宜佳是什麼,我說宜佳是時下女孩子們的夢想之一。他說這種說法他覺得很奇怪,而且他老婆也沒跟他說過。我想,至少對於這所房子而言,我和他都是陌生人,當然性質不同。
他一路上脫掉了T卹,又脫掉了牛仔褲,直接就進了盥洗室。在噴淋的嘩嘩聲中,他叫我也去洗個澡。我猶豫著站在了客廳中間,那裡依然掛著幾幅他老婆的大美人照。我環顧四周,發現房間裡並沒有什麼異樣,可見,香格里拉之後,他們似乎誰也沒有回這個家。我剛疲憊地坐在沙發上,吞吐就圍著浴巾出來了。他說,趕快去洗澡呀,你放心,我老婆說了,我不回德國,她不登這個門!
那是我們最後一次在一起。我們彼此都好像懷著深仇大恨。恨恨地不願放過彼此身體的每一個角落,直到筋疲力盡了才不得不放棄。
第二天我醒來的時候吞吐還在酣睡。只見他本能似地把腦袋扎在薄被子裡,我只能看到他結實的背和白皙的皮膚。我凝視了他一會兒,覺得除了這一場睡眠以外,此前的一切都十分不真切了。然後,我悄悄地起身,離開了。
好像是心照不宣似的,那以後,我們誰也沒有與對方聯繫。一周之後,我收到了他的E-mail。他的信是這樣寫的:麥芽兒,我現在在機場,很快就要登機了。最初,是你延長了我在國內逗留的時間,現在也是你讓我突然離開了。我說不清我還會不會回來了?那天晚上在香格里拉,我看見了你想讓我看見的一切。不幸的是,這是我不想知道,也不想看見的。他還說,婚姻其實很簡單,它就是一張紙,經不起捅。你不捅破它,它就會存在。
這封信很短,我卻反复看了好幾遍,然後把它下載到我的信夾子裡。
我沒有回信。
現在,事情已經過去兩個月了。我沒有得到他的消息,也不想給他寫信。我經常想起他的眼睛,想起跟他在一起的種種快樂,我無法給我自己一個解釋。既然我獲得了快樂,既然我早已不在乎一個男人“使君有婦”的歷史而懂得享受;既然在多少個被寂寞啃嚙的深夜我依然認定我寧願使我和吞吐相聚的每一個時刻都漲滿激情,而不願在味同嚼蠟中朝夕相守;也既然,坦率地說,即便是吞吐,也不值得我以大張旗鼓的拼搶方式給自己套上婚姻的枷鎖——婚姻,就是一對癡情男女海誓山盟地自願朝里鑽,還常常夭折呢,掐住一個男人的脖子,雙雙引頸就縛,又會有什麼好滋味呢!我不想扼住一個有婦之夫的咽喉,也就是不想把自己逼到懸崖的邊緣。那麼,我幹嘛要定下這個特異的約會,請君入甕呢?不,應該說,我幹嘛要以這種方式,使吞吐成為他妻子秘密約會的致命殺手呢?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後悔。
我還是照常在午夜以後去拾荒者,還是獨來獨往,一個人在吧台喝一小杯馬爹利,跟誰也不搭話。但許多問題總是混亂地糾纏著我,使我不得安寧!
這個世界謊言太多,各取所需的偷情算不算謊言?
這個世界背叛太多,並未導致離婚的紅杏出牆算不算背叛?
這個世界惡貫滿盈,是不是這種謊言和背叛已無足輕重?
人是高級動物,情感世界不能不豐富、迷人和復雜,是不是應當有法律或道德之外的考量標準?吞吐承當著我這樁遮蔽,會不會對他合法妻子的蔭翳假裝不知道?
吞吐跟我在一起,是不是在跟他老婆維持一種微妙的平衡,以便雙方在心照不宣中引而不發?
合法婚約在那一張紙之外是什麼?
愛情是什麼?性在愛情中處在什麼位置?
誰能為我解答這些問題呢,只怕就是有人來解答我也不會信服的。我記得小時候我讀過繪本寓言故事盤古開天闢地。講的是以前天和地相接如一顆大雞蛋,一片混沌,烏煙瘴氣,盤古揮舞一柄大板斧,上下一陣狂舞,於是,天成了蔚藍的天,地成了土黃的地,人類開始繁衍。
盤古是一個盡情盡興的舞者。盡情盡興所以快樂,這是我一貫的信奉。可是我盡情盡興之後,快樂總是大打折扣。也是,盤古不僅是神,而且還是一個男神,我怎麼能夠妄想像他那樣痛快地開闢一個新天地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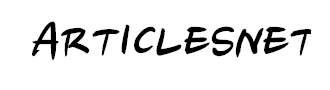













![[蘋業配] 就要過年啦!你還不快買台 Apple TV 回家讓你家中長輩上 NETFLIX 輕鬆看電](https://www.iarticlesnet.com/pub/img/article/72528/1453458107512_xs.jpg)
![[蘋業配] 神癮少女年終大許願!到底少女們希望老闆送她們哪些蘋果產品咧~~](https://www.iarticlesnet.com/pub/img/article/72514/1453393309380_xs.jpg)
![[蘋業配] 買 Mac 超簡單!六種型號特性大不同,搞懂之後就能輕鬆入手最適合你的蘋果電腦~](https://www.iarticlesnet.com/pub/img/article/72501/1453357305378_xs.jpg)
![[蘋果急診室] 誤刪資料也不怕!OS X 內建 Time Machine 幫你自動備份資料,還能還原](https://www.iarticlesnet.com/pub/img/article/72430/1452774103746_xs.jpg)




![不喜歡用 iPhone 套 這個套適合你 [圖庫+影片]](https://www.iarticlesnet.com/pub/img/article/67749/1415708430630_xs.jpg)





![[25 3] iPhone iPad 限時免費及減價 Apps 精選推介](https://www.iarticlesnet.com/pub/img/article/2004/1403780749621_xs.jpg)